距离长和集团与贝莱德财团原定的港口交易签约日仅剩24小时,这场涉及228亿美元、牵动中美地缘神经的世纪交易突现致命转折。3月2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对交易启动反垄断与国家安全审查,长和被迫推迟签约计划。
然而,这场看似暂停的博弈却暗流涌动——长和近日被曝计划分拆估值超150亿英镑的全球电信资产,并寻求伦敦上市,被外界解读为“转移资产”的信号。


这场交易的复杂性远超商业范畴。长和拟出售的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控制着全球6%的贸易流量,中国21%的商船需经此通行。美方若通过贝莱德掌控港口,可对中国货轮加征“政治附加费”或限流,直接威胁“一带一路”供应链稳定性。外交部、商务部、港澳办三部门罕见联合发声,直指交易“损害中国正当利益”,为事件定下政治基调。
李氏家族的“后手布局”:从“港口风波”到“资产转移”

长和的应对策略暴露其深层焦虑。3月30日,长和紧急发布公告,否认分拆电信业务的传闻,但措辞耐人寻味——“未做出任何交易决定”的表述,实则为后续操作预留空间。这一操作被解读为“风险隔离”:若港口交易引发中方全面制裁,分拆后的电信资产或成家族退路。
然而,这样的小算盘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其一,英国工党政府正推进关键行业国有化,2024年11月通过的铁路国有化法案已敲响警钟。若长和电信业务赴英上市,恐遭政府干预甚至强制收购。其二,中国市场反噬已现端倪:长和股价在审查消息公布后单日暴跌3.54%,市值蒸发781亿港元,其在内地的地产、能源项目遭国企合作冻结。
更致命的是,李氏家族内部出现裂痕。次子李泽楷旗下盈科集团迅速与长和切割,独立运营的富卫保险、电讯盈科等业务被视作“家族防火墙”。这种“弃车保帅”的策略,也能看出李嘉诚对局势的判断是悲观的。

从舆论战到法律围剿:官方“制度武器”全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据《反垄断法》与《国家安全法》,将审查范围从交易本身扩展至长和全球资产结构;港澳办引用香港国安法域外适用条款,警告“损害国家安全将追溯追责”。这种立体化监管体系,令长和陷入“进则触雷,退则违约”的绝境。

贝莱德的“双面困境”
作为交易的另一主角,贝莱德深陷舆论漩涡。这家管理10万亿美元资产的巨鳄,既是小米、比亚迪的重要股东,又深度参与中国地产投资,却在港口交易中扮演地缘推手角色。其董事长拉里·芬克在致投资者信中,将港口称为“主导未来发展的资产”,却避谈中美博弈风险,暴露出商业逻辑与政治野心的冲突。
全球港口权力重构:中资“替代方案”浮出水面
面对美方围堵,中国早已未雨绸缪。秘鲁钱凯港、巴西圣路易斯港等“一带一路”枢纽加速建设,未来可分流巴拿马运河30%货运量;中欧班列2024年开行量突破2万列,北极航道通航期延长至8个月,进一步降低对传统航道的依赖。

反观美国,其霸权逻辑正遭遇反噬。2024年中美芯片战中,中国砍单970亿颗进口芯片,导致美半导体企业市值蒸发27.6万亿元;若港口交易引发中方稀土管制升级,洛马公司F-35生产线或面临瘫痪。
总结

长和交易风波,本质是全球化退潮下跨国资本的生存困境。李嘉诚的抉择,不仅关乎商业利益,更触及企业家责任与民族大义的红线。若执意交易,短期套现190亿美元的代价,将是失去中国市场、家族声誉崩盘;若终止,则需直面美方施压与巨额违约金。
正如《大公报》所言:“商业决策若只求一己之私、漠视国家利益,终将遭国人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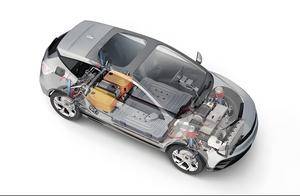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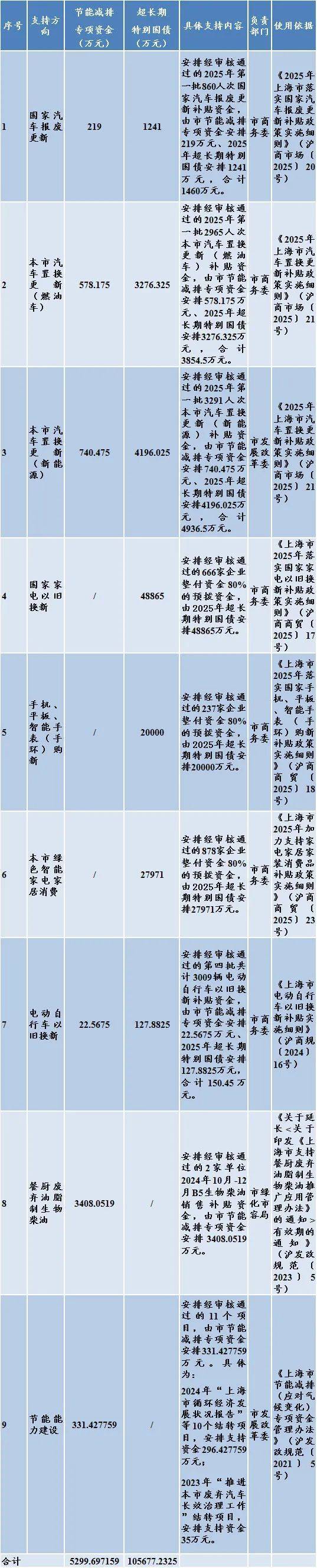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