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成长定价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即成长要可持续,并且能够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的成长才是真成长,只有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够持续地创造价值。
本刊特约 王雁飞/文
无论是价值股投资还是成长股投资,它们估值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建立在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价值股投资和成长股投资都绕不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判断企业的增长率以及如何为企业的成长性估值。
警惕“伪成长”
在《投资者的未来》一书中,杰里米·西格尔通过IBM和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投资案例,揭示了投资者在长期投资中容易陷入的“增长率陷阱”(Growth Trap)。假设1950年投资者需要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进行长期投资,并将所有分红再投入,直到2010年才能卖出。作为一家非常有前景的高科技企业,IBM的增长能力远超标准石油公司——事后看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由于IBM估值长期较高,从长期投资回报来看,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投资回报反而表现更好。典型的成长陷阱就是投资者有追求高增长率公司的心理倾向,而忽视了估值和股息回报的重要性,从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不如预期。
从现金流折现估值原理不难看出,短期的高增长对于企业内在价值的增厚作用非常有限。现实中多数企业的成长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我们不妨以沪深300成分股(剔除增速超100%的异常值)为例,来看看成长的随机性有多强。
图中纵轴为EPS(每股收益)增速,横轴为成分股企业按2021年的EPS增速值从小到大排列,2021年的增速散点就连接成了一条红色曲线,绿色散点是同一家成分股对应的2024年三季度的EPS增速值。有两个重要发现:2024年三季度增速与2021年离散特别大,即成长具有强随机性;2021年EPS高增的企业,在两年零三个季度之后绝大多数下滑,即存在明显的“成长陷阱”。
除此之外,低质量的成长同样值得警惕。
笔者最近关注了一家港股上市企业,作为行业领头羊,其过去10年盈利稳定增长,2023年归母净利润18.22亿元,较十年前的1.35亿元增长了十几倍,年化增长率高达26.69%,累计实现净利润126.72亿元,在很多投资者眼中俨然是一家高成长性企业。
然而,该公司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市场份额,不断大量投资产能,过去10年间累计资本开支148.84亿元,但资本开支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经营现金流入。近10年累计为股东创造的自由现金流仅41.39亿元,远低于同期账面净利润。由于无法内生性增长,企业只能通过融资发展,其带息债务占全部投入资本的比例已经由前几年的20%增加至47.25%,这样的发展模式不仅积累了较高的风险,而且让企业没有能力持续高额分红来回报股东。
成长是否创造价值?
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在《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中指出,投资成长股(指有成长的公司,包括通常意义上的价值股和成长股)的回报率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股息回报率;二是公司在核心市场可能的“有机增长”,这通常由市场需求自然增加所带来,比如可口可乐的全球化经营或白酒的提价;三是留存收益再投资可能创造的未来回报。
就第三点而言,多数企业要想增加收入,既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又需要增加应收账款和库存,但股东对这些再投资的回报率是有要求的,要高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或股东的机会成本。只有这样的成长,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
假设有一家公司新增投资10亿元,每年增加净利润8000万元,投资回报率8%。这是不是一笔好投资,有没有增加企业价值?如果企业的资本成本是10%,或者说股东预期能够带来10%的回报率,那么这些利润所带来的价值就是8000万/10%=8亿元。与企业的再投资金额10亿元相比,很遗憾这笔投资没有真正地增厚企业的内在价值。
对于“成长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巴菲特给出了自己的衡量标准。他认为资本开支是企业为成长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观察“实现1美元税前利润增加,需要多少美元的资本投入”来衡量再投资回报率,通常要实现1美元税前利润的增加,需要5美元的资本投入,亦即20%的再投资回报率。
从这个角度看,这家新增投资10亿元的公司的成长含金量没有达到巴菲特的标准。再看上述港股公司的例子,尽管在过去10年里这家公司净利润从1.35亿元快速增长到18.22亿元,但同时期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存货累计增加了184亿元,再投资回报率低于10%,属于巴菲特所说的“被迫留在游戏中”的生意。
无论是布鲁斯·格林沃尔德说的“有机增长”还是留存收益再投资所创造的回报,“成长是否创造价值”这个问题最终都落脚到“企业是否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上来。首先,“有机增长”是罕见的,只有像可口可乐、喜诗糖果、贵州茅台等极少数企业才有机会不增加资本开支就获得增长。其次,留存收益再投资所创造的成长有赖于护城河的保护,在没有进入壁垒保护的情况下,追随者会加入到游戏中来,把最初的高回报率拉下来,最终所有竞争者都只能赚取与资本成本相当的投资回报。
因此,为成长定价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成长要可持续,并且能够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的成长才是真成长,只有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够持续地创造价值。
为成长定价
成长的理想价格,最好当然是零:投资者所支付的对价与当下的资产价值或盈利能力价值相当,免费获得未来的成长性。这是格雷厄姆对成长的处理方法,即不理会对美好未来一厢情愿的乐观预测。遗憾地是,现实中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
我们这里讨论“为成长定价”时,“成长”隐含的意思是“长期成长”,是只针对于拥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而言的。无论是价值股还是成长股,投资者都要认识到成长预测的极大局限性:短期的高成长不改变内在价值,长期的成长预测存在重大偏差。只有极其少数拥有高护城河的企业,才具有定价的基础。
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对成长估值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有试图计算的方法总会遭遇重大挑战。只有最严苛的条件下、有高壁垒和确定性的增长条件下,才可能对成长的价值进行精确的计量。
不妨看看巴菲特对这样的企业是如何定价的。
伯克希尔的投资经理库姆斯曾说,他周六常去巴菲特家交流,关于企业评估,他们经常会用这样一种测试:巴菲特会问未来12个月会有多少家公司到15倍市盈率?有多少家5年后赚得更多(置信区间90%)?有多少家会达到7%的复合增长率(置信区间50%)?库姆斯说他们就是用这个方法找到了苹果。
15倍市盈率意味着买入当年的收益率6.67%,第10年期的收益率达到6.67%×(1+7%)^10=13.11%,整个十年间的累计收益率为98.55%,折合年化收益率约10%。格雷厄姆认为,当收益率高于无风险收益率2倍时,股票相比于债券更有吸引力,巴菲特的预期收益率可能略高一些。巴菲特早期投资的很多没有成长性的低估值公司市盈率多不超10倍,可以认为他的预期收益率是10%左右。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同样的确定性之下,“15倍市盈率和7%增长的企业”和“10倍市盈率无增长的企业”基本等价,二者都能取得10%左右的预期收益率。这就是巴菲特对成长的定价方式,他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没有放弃预期收益率要求,这个15倍市盈率是巴菲特愿意为“成长”所付出的溢价。
(作者为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投资风险自负)
本文刊于01月25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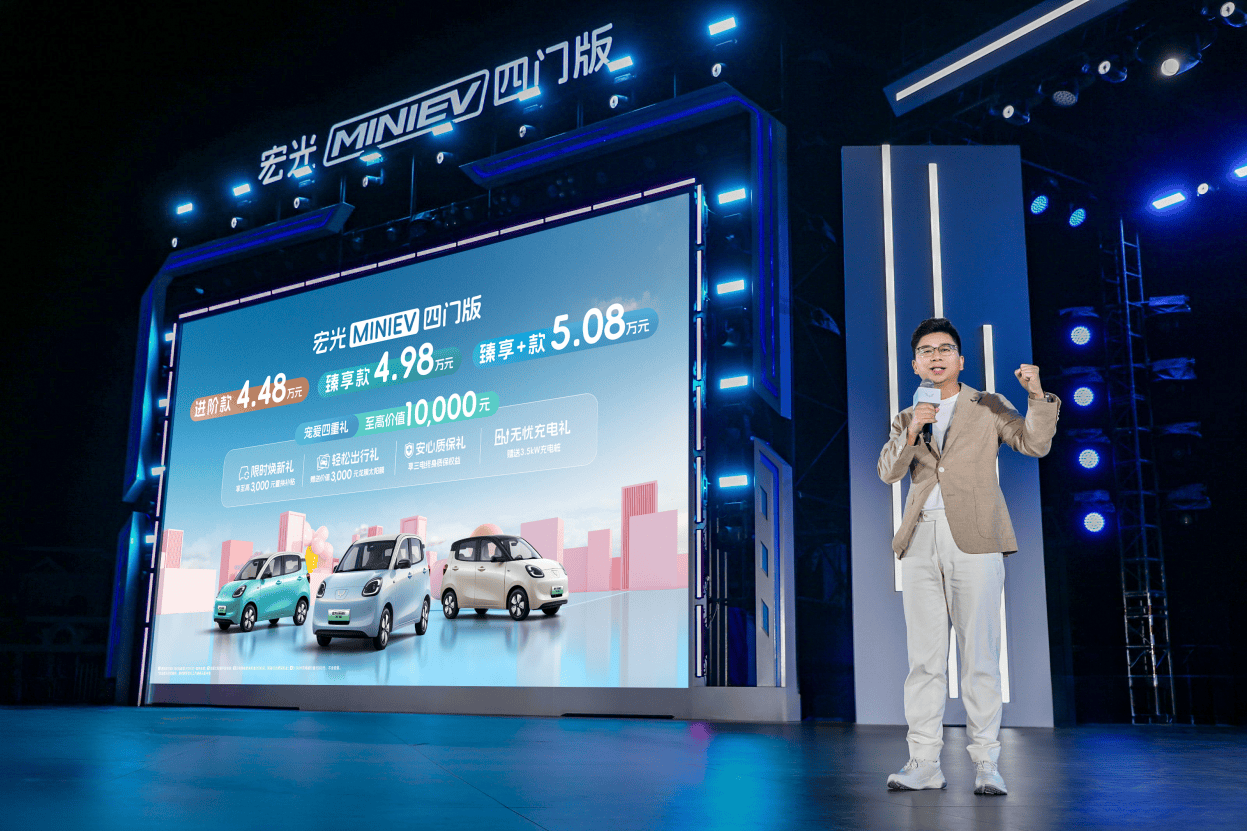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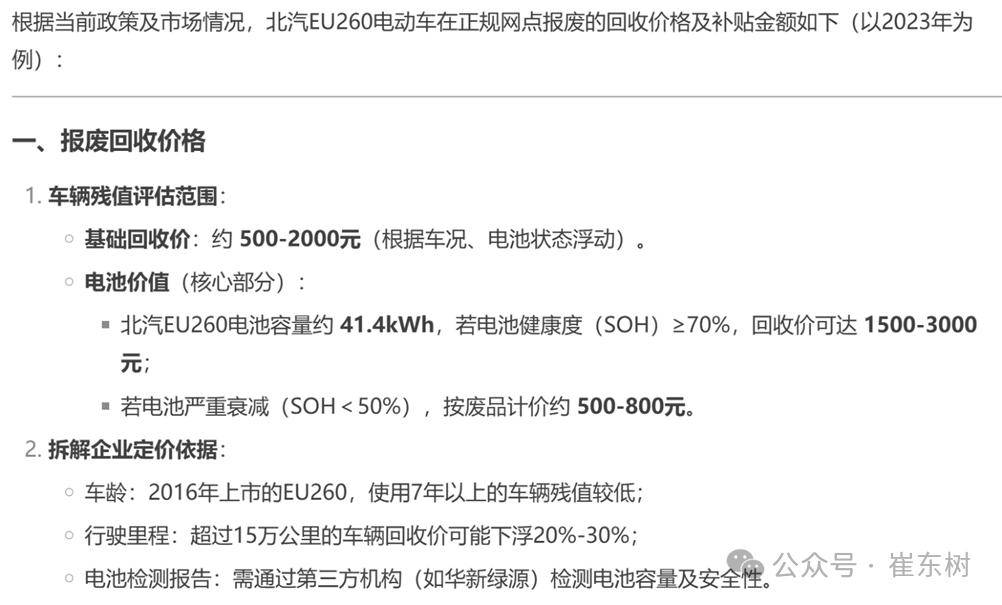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