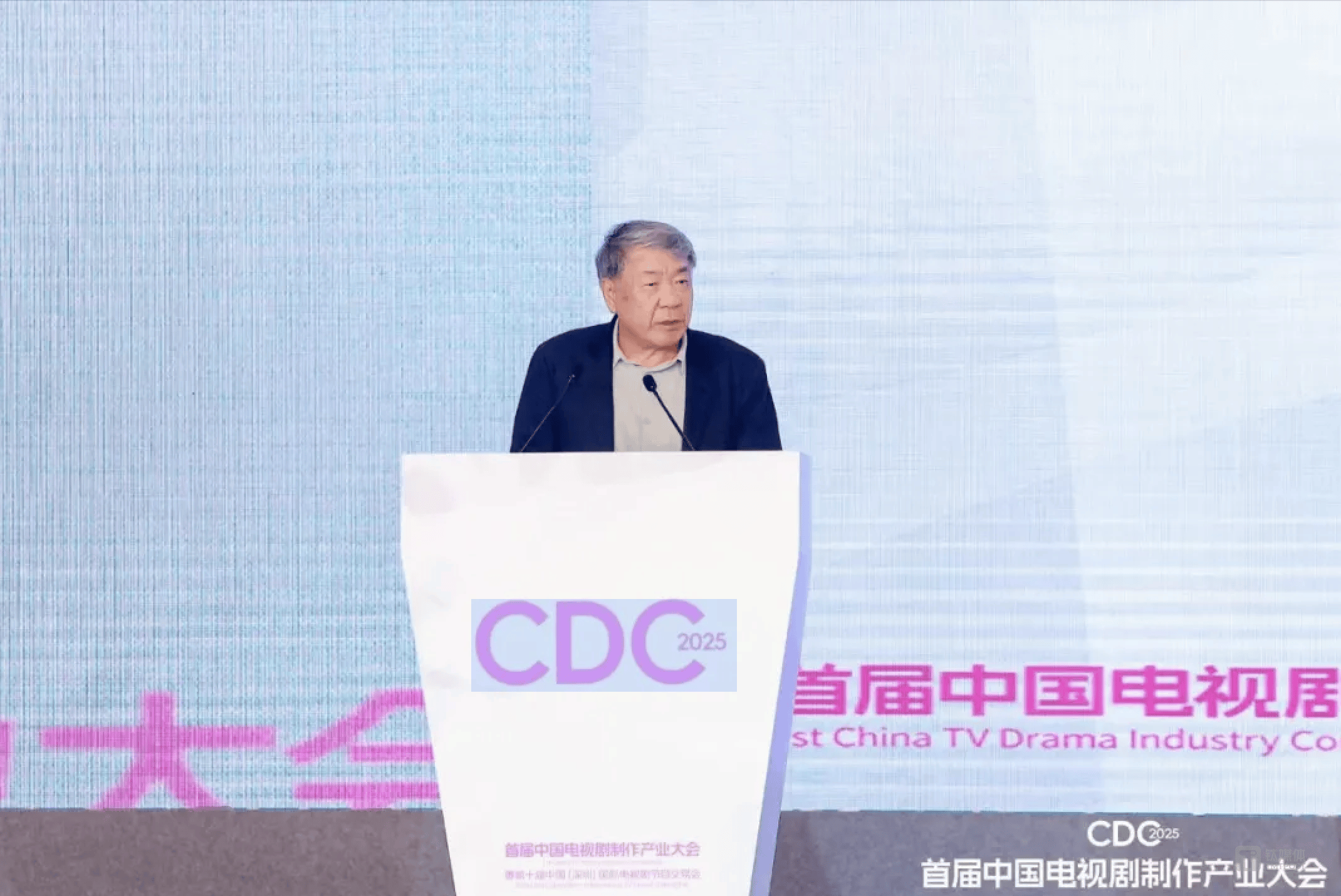
著名导演郑晓龙,图片来自首届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
在今年首个电视剧行业大佬到场最“齐”的大会上,,认为其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搞排他,“十分糟糕”,要“保护行业健康发展杜绝垄断”。
龚宇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电视剧制作协会常务副会长,后者是一家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的行业团体。他的公开发言,犹如一枚炸弹,再次将长剧与短剧之间的矛盾摆到台面上来。
而就在上个月,。而独家了解到最新进展是,双方合作确已搁浅。而其中,红果的“排他协议”,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对于一些被迫卷入“平台之战”的中小短剧公司来说,与红果短剧签约独家之后,的确能够感受到剧集有平台流量的加持,不过,至于后续作品能不能上爱奇艺,倒不是他们最关心的。
让他们比较费解的是,协议期内,短剧如果上线了同为字节跳动旗下的厂牌“抖音短剧”,也就是抖音平台的各大端,也会触发红果的“排他”条款,被红果方面起诉至法院。
与此同时,,同样拥有超高DAU的超级互联网平台,也大力加码短剧赛道,并给出了丰厚的扶持策略,让很多已签约红果的短剧公司无法参与其中,也倍感遗憾。
而又因为,现在制作方都盯着流量排行榜单跟风创作,过了协议期的内容,再上其他平台已经意义不大。
不过,行业内普遍的共识是,无论与哪家平台签署“独家协议”,都属于双方自愿,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并且,还独家了解到,红果短剧提出的创作周期“排他协议”,也并非面向所有的短剧公司。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竞争迫使行业内各方暗涌已久的矛盾再度公开化。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会上,另外一则对微短剧批评声音相当之“重”的言论,也引起了舆论热议的,则是从著名导演、中广联合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会长郑晓龙那边发出。
郑晓龙认为,“随着微短剧的火热,市场上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导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不合常理、违反常识的微短剧一度被观众追捧,获得超高的播放量,甚至长期霸屏。这些作品中,低俗媚俗、暴力血腥、色情擦边等问题不断显现,冲击着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扭曲了价值观,且套路化和逻辑混乱等问题日益严重。”
“屌丝逆袭、极端复仇、穿越重生、甜宠虐恋等等,这些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微短剧中得到满足和释放。这些所谓的‘爽感’,让微短剧有时被称为‘电子鸦片’。这些白日梦的编织,对年轻人,尤其是对未成年观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潜在的误导。”郑晓龙如此斥责。
比起龚宇演讲中最后直接点名,表情还略显犹疑,郑晓龙对微短剧的这番批评,不可谓不“重”,也引起了各方争议。
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人代表性人物,郑晓龙是熟悉市场化规则、内容创作和观众偏好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内地电视剧产业史上,郑晓龙都是当之无愧的“爆款制造机”。他参与制作的《渴望》首次让观众知道了什么是电视剧,策划的《编辑部的故事》是国内情景剧的先河,而编剧、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是中国第一部在境外拍摄的剧集。
郑晓龙执导的题材多样,从《金婚》到《甄嬛传》,引起过“破圈”的轰动,成为了经典,甚至变成了一种现象。
比如说,《甄嬛传》不仅捧红了很多演员,剧里很多配角,比如,蒋欣、谭松韵、毛晓彤、唐艺昕和热依扎等,后来都成为娱乐圈炙手可热的艺人,还催生了一群深入研究剧中桥段、人物性格、台词表演、饮食文化等细节的“嬛学家”,他们自发把剧中的人物制成表情包,在社交平台上各种“二创”。
郑晓龙在影视圈的号召力始终强劲。《甄嬛传》开播13年,就在上个月,他还把当年剧组核心主创聚在一起,组织了一场《甄嬛爱不停——甄嬛传小主节晚会》,也被很多剧迷们称之为“超强售后”。
在当时与郑晓龙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交流,话题围绕短剧展开。
在那一次交流中,郑晓龙对短剧的看法表达十分中肯,认为影视剧创作,长、短并不是关键,一个好的艺术作品需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把短的抻长,但是也不要把长的故意把它砍短。你只要是有话认真地的创作,长也是可以,短也是可以的。”郑晓龙对说。
某种程度上,现在,大家拿着显微镜看《甄嬛传》,赋予不同情境下的“二创”解读,既是对这部剧历经时间考验水平的肯定,也是一种对当前影视行业内容创作的无声的不满。
以至于,但凡出现一部尊重观众的诚意之作,大家都跟“吃了大补丸似的,天天倍儿精神”,争先在社媒上当起了“自来水”。
今年(1月28日-2月6日),有第三方平台发布的网络舆情数据显示,档期内数据最高不是《哪吒之魔童闹海》,而是另一部有流量明星参与的影片,并且持续遥遥领先。,甚至力压追逐流量的微短剧。
而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影视行业,仿佛都看不到观众的需求。
在万事万物急速变化的当下,因为电影和长剧的制作周期相对较长,且受诸多因素影响商业风险高,不难理解行业会陷入一种集体迷茫的状态,但对整个影视剧行业(也包括微短剧),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
以下是与郑晓龙的对话实录:
:时隔13年,《甄嬛传》剧组再聚首,您有哪些感触?
郑晓龙:我还是挺高兴的,最主要的是在这时候见到当时合作的创作者和演员,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只有拍戏的时候见,不拍戏的时候,也就见不着。
另外,让我自己感到有点意外的,从一开始拍,到上线播出,《甄嬛传》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喜欢,除了原来的老观众以外,还有很多年轻观众成长起来了,也开始来看《甄嬛传》,并且也喜欢《甄嬛传》。
这让我很意外,也很高兴。因为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是有时间的生命力,有时间生命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我觉得时间最能说明问题。我们说过去一直说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大浪淘沙历史把它留下来的作品,那就是好的作品。
:您提到了时间对作品的考验,我们会感觉到,这几年行业变化挺大,尤其是最近两年,一些新形式的作品也比较受观众喜欢,比如说短剧。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很好奇,行业内还有可能产生类似于《甄嬛传》这样的作品吗?
郑晓龙:现在新一代的创作千万不要,比如说,这个题材火了,我就遵循着这个去做,跟风你永远跟不上。短剧出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有长剧、短剧。影视剧创作是这样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把短的抻长,但是也不要把长的故意把它砍短。你只要是有话,认真地创作,长也是可以,短也是可以的。
原来我们的电视剧的发展从最初就是从短剧开始,第一个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注:1958年我国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仅1集,20分钟),中央电视台的,就一集,它就是短剧。
我知道很多年前,30年前,中国电视剧设立了个“飞天奖”,其中有一个奖项当时设置叫丰收奖,所谓丰收奖就是一个单位,当时没有私人,没有民间拍电视剧,都是国有的电视台或者专门的制作单位。一个单位所拍的电视剧一年加起来达到了15集,就是飞天奖的丰收奖。
最早的“白玉兰奖”,我去当过评委会的主席,当时没有长篇连续剧评奖,都是短剧。所以说,短剧是非常正常的,原来我们就有这种剧。但是近些年电视剧拍得越来越长,这个跟电视台希望电视剧长的广告要求有关,这是一个时代的情况。
这些年随着网络的播出,观众对电视剧的要求变得更多样化,短剧也慢慢兴盛起来。前几年我拍了一个片子,和一批朋友一起,叫《功勋》,每一个人6集,就是短剧,每一个人物,我们拍他生命当中最辉煌的一段,并不是非要拍他的整个人生,它就可以长和短,可以有要求,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现在问题不在这儿,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有一个微短剧,竖屏剧。大家现在都说横店不叫横店了,叫“竖店”了。我见他们横店老总,说横店一年差不多有上千部戏的微短剧。
微短剧就是一个新的样式,它跟短剧的样式不一样,短剧它还是按照人讲故事的方式,蒙太奇的组合的方法讲。微短剧已经从结构上可能不一样了,它讲的核心内容也不一样。
微短剧现在出来的很多,而且也很抢收视,但是比起长剧、比起正常的电视剧,它仍然是非常少。在我看来,短剧需要大量的实践之后才能够有理论去总结它,因为这个实践量太少。现在真正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像我们说的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还很少。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更复杂的短剧。但是,微短剧要迎合现在观众希望短时间内就看到一个片子,希望短时间内解答一个问题的这种节奏,那和我们过去文艺作品想要表达的,比如说社会现实,人物内心,复杂的人物个性与内心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能不能持久?作为一个文艺作品,能不能长时间地持久发展下去?我看还有待观察。这是我对微短剧的回答。
:您认为《甄嬛传》的成功现在我们还能复制吗?
郑晓龙:干嘛要复制?我们自己再去创造,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再复制,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题材,更好的故事,更好的演员来拍出更好的片子。所以说复制我觉得很难,而且那个时候和现在也不一样。现在的观众,创作,审查标准都不一样,所以说照着原来复制够呛。
但是你要说可能会不会以后,还出现这种能长时间地产生社会效益和观众喜欢的作品,我觉得将来一定会有。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聪明的人,这么多创作者,怎么会没有这样更好的片子?所以说,要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它是可以复制的,我们照样可以拍出来比《甄嬛传》还好的片子,我希望是这样的。
:您认为现在新一代创作者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您有没有比较看好的新一代年轻的创作者,或者优秀的创作表达?
郑晓龙:我觉得有些方向性的问题,比如说还是按古装偶像、古装仙侠或者是这个路子去,只能一时,不能长久,我觉得文艺作品的落地,去表现人和复杂的人性,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人本身是什么?说实在话,人还是个群居动物,他还是希望了解人的生活,人性的东西,你的作品不会这么表现,就表现漂亮,那肯定不可能成功。而且,对美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或者是不同的标准。唐朝觉得以胖为美,现在以瘦为美,不一定什么时候以什么为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本文首发于,作者|李程程)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