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长三角momo 祝颖丽
阿允(化名)找现在这份工作时 30 岁,这是她的第四份工作。以往每次面试时,她都会被问,“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有打算结婚吗?”
这次也不例外。照以前,她会如实回答。但这一次,她决定反问回去。
“为什么你们每一个面试官都要问女性这样一个问题?”她向对面那位一直在反驳和否定自己过往的男性面试官发起“挑战”。
她知道得不到什么很好的答案,但通过提问,她想扭转一个育龄女性求职者被动的感受;她想通过把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正式地提出来,让人意识到必须问出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就是一种“问题”。
面试官果然先是惊诧了一下,瞬即回到自己的逻辑,“我当然要问,我招员工,当然要掌握家庭情况。”
这不是一场愉快的面试,但阿允感受到,通过问这样的问题,她作为一个女性求职者,开始找到一种更主体性的感觉,“就是一些微小的反抗。”
这次之后,她开始关心面试官和他/她背后所代表的公司的性别观念和男女用工差别。她有意识地问对方公司女性管理者的比例,女员工的比例。
有一次,一位面试官真诚而又疑惑,问她,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对你的求职很重要吗?
阿允很难解释,她想做的是打破某种对惯常的“漠视”,也想测试一下在舆论场上激烈讨论的“女性主义”落到线下,大家真实的敏感度和意识进步到底如何。
“你会发现,还非常不够。远远不够。”几次实验后,阿允总结她的观察。
职场女性依然是“第二性”
今年37岁的文西(化名),人生的前半段都在一种她自称“超绝钝感力”的状态下度过。
出生时,祖辈和其他亲戚会惋惜“怎么生了个女儿”,但父母从没说过什么;高中学理科,也听见“男生就是比较聪明、后劲足”的声音,但她自己就是那个更聪明的人;大学时,大家默认男生更懂电子设备,东西出问题了找男同学修,但她从小鼓捣这些东西,,在宿舍里替代了“男同学”的作用。
直到开始实习,她突然成了一个需要端茶倒水的人。起初她说服自己,职场新人嘛,就是要从杂活干起。她的工作要社交,有时候男性在一起拿女性开些黄色玩笑,她也觉得要“大度”,要融入大家。
她记得有一年苹果手表面市,男同事们又开始了“玩笑”,称苹果表为苹果“婊”,她照常附和、和大家嘻嘻哈哈。
一位比她年长、职位也更高的女领导私聊她,“你是个女性,怎么也能像他们一样说呢?”
她突然感到被什么东西劈了一下,过去各种微妙的不舒服累积至此,突然有了一个线索:女性这个性别似乎惯常就是被贬低的。
相关的记忆开始涌现。她记得,有一次她在网上发帖,从技术流的角度分享自己音箱、耳机时,论坛的编辑主动给她的帖子更名为“女汉子的设备体验”,她觉得怪怪的,能感受到一些“认同”,但又觉得扭曲。
还有一次,她帮一位男性领导解决了个技术难题,对方先是夸她,“很酷啊”,随即又找补一句,“女生不用这么拼,代码这种事情交给男生就好了。”
到此时,一些问题变得清晰。她回想起过去每当她表现得好时,都会被赞美“厉害得不像一个女生”——但她明明天然就是一个女性,她从来就理科很好、会修电脑,喜欢电子设备,“这些不对劲累积多了之后就会开始去想,是我有问题,还是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意识是不对的?”
更年轻的女孩李敏(化名),更早就觉察到这一点:女性在这个世界是“二等公民”,是男性眼中的一种性资源。
酒局是这种感受最集中体现的地方。李敏 1995 年出生在山东,这是一个酒文化浓厚、有很多酒局的地方。她总结,酒局就是主要以“女性倾听男性的发言,为男性捧场” 的地方。
走出山东,酒局再次冲击到她的是一次实习经历。那是一家知名的投资机构,与金主觥筹交错是常事,长得有些姿色的年轻女员工往往成为酒局为大佬们捧场、助兴的角色。
老板第一次带她去酒局时,言语矫饰,说去了能帮她认识很多人,以后也许有各种内推和实习,对职业经历有好处。
但去了之后,李敏才弄明白自己作为“配菜”的真相。她从小就在反抗敬酒,但职场的酒局迷惑性很大。除了老板的说辞,她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诱惑,如果能通过姿色获取大佬的青睐,人生之路是不是可能更顺?
但本能的不舒服在拉响警报。她感到恶心、抗拒,难受了很久,当第二次要被带去类似场合时,她提出了离职。
她开始清晰地看到年轻女性可能的处境,她意识到这是一条不正常的道路,“或者说这条道路肯定是代价更大的。”
这段经历给李敏留下的印记是,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打扮,不敢让自己被当做一个好看的女性被注意到,她害怕再次被当做猎物。
早在 70 多前年,哲学家波伏瓦就点出,男性通常被视为“主体”或“默认的存在”,而女性则被定义为“他者”,是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女性不被鼓励探索自己的独立潜力,而是被为驯化为更适应男性需求的角色。
到了21世纪,女性仍无法摆脱被当做“第二性”的目光,哪怕是在职场。
阿允也记得,一次工作聚餐中,一位男老板话头不知怎么拐到了评判女员工身上。这位男老板和几位男同事开始讨论哪位女性最适合当人妻。最后他们共同选中了一位刚结婚的、不在场的女员工,一致认为对方最符合他们心中“贤妻良母”的形象,说完几个男人不怀好意地咯咯笑。
另一份工作中,阿允所在的组女生多,唯独领导是一位男性;一次,另一个部门的男同事找来,推门后第一句话是,“某某总你好有福啊,一屋子全是美女”。
“我当时听完就觉得就犯恶心。”阿允回忆道。
但冒犯无处不在,即便突破重重障碍成为一个女领导,偏见也不会减少,比如说她们“太喜欢抠细节”、“更容易紧张焦虑”,总结起来都是:女老板不适合团队管理。
做到中层管理的文西,更大的感触是女性常常被低估,成果被“摘了桃子”。当时她在一家做内容的互联网大公司,她所在的业务部门中层骨干全是女性,但她们共同的领导是个男性。
文西形容他们这个组合就像《红楼梦》里一道菜“茄香”——用十几只鸡的鲜味煨一根茄子,“那帮男的就是那个茄子,就是个破茄子。他们能当领导,是需要十几只鸡来配他。”
她看到的是,这位男领导几乎什么都不会,所有脏活、苦活、累活、技术活都被分配给了下属的女性,而他踩在女性的努力之上得到权力后,管理的手段却是打压。
文西有一次被这位男领导带到小黑屋,对方跟她说,“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成就,全都是因为我给你们的环境,都是我的功劳。”
这位男领导极为厌女。不仅不认可女下属的价值,也会在公司贬低自己生了两个孩子的妻子,“他自己明明把活都给我们了,在公司一边打游戏,一边跟我们说,‘真羡慕我老婆,不用上班,就在家带我两个儿子,什么都不用做’。”
文西观察,这种配置和状态很普遍,这家公司的其他业务部门通常也都是“一个茄子需要十几只鸡来配”,“就是真正主力干活的,忙前忙后的都是女性,但最后被提拔上去、或者空降下来的领导都是男的。”
2023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深度调研了八家中国企业的性别平等实践,其中包括京东、联想、华为、厦门航空、太平洋保险等各行业的公司。
这份名为《工作中的女性——中国企业促进性别平等在行动》报告中显示,即便已将“性别平等”当作目标的企业,其女性员工占比最高也不到一半,最少的只有20%。
进入高级管理层的女性比例就更低。《工作中的女人》提到,“由于对性别平等的投资不足,全球妇女在管理岗位中的比例为 28.2%,按照目前缓慢的变化速度,到 2050 年,妇女在职场管理岗位中的比例将仅达到 30%。”
当女性有了新目光
韩国女作家韩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时,泛文化类播客《随机波动》的主持人张之琦发了一条微博。她写道,暴言:是诺奖需要韩江,而不是韩江需要诺奖。
她的意思是,诺贝尔奖也需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东西,而女性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尽管变化很慢,但一个好迹象是,女性在舆论场上的声音似乎也在变大。
在中文互联网上,今年女性脱口秀演员数量在变多,话题也更多元,她们讲卫生巾羞耻,讲婚恋难题,讲母女关系,讲从原生家庭逃离的贫困女性,讲一切女性视角看去的体验和荒谬……她们说要“上桌”,要“吃好”。
而当这一切浸染到职场,女性的目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刘芳(化名)是今年毕业的应届生,刚工作三个月,是一名互联网大公司的运营。她看到,在运营这个女性居多的岗位上,即便是女老板也会无意识地说要招些男性,很多时候甚至会破格录取,“但美其名曰性别平衡。”
性别互换下,这种不公平的意味就很明显,比如在以男性主导的领域时,女性很难仅仅因为性别被破格录取,甚至可能首先被质疑能力。
刘芳意识到,“男生居多的时候是男生擅长;男生占少数,大家会觉得男生稀缺。擅长和稀缺都是一种觉得他们很珍贵的词。”
实习过几家大厂的刘芳还看到,职场似乎天然就不是为女性设计的,“互联网大家讲究效率、竞争,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想要的那种人,塑造的文化,它是有模板的。比如强调你要激进,要争夺很多东西,这种狼性文化一直都是社会对男性成长的要求。”
她看到那些不生育或者出了月子立马就来工作的女性,本质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可以像男人一样,“但对女性来说,这是在过度损耗自己身体。”
这种新的目光,并不是每个女性天然就有的。
文西的觉醒,她自己形容是从完全蒙昧到知道自己不知道,再到知道自己知道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些意识先锋的女性主义博主在她的启蒙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文西还记得自己关注了一位女性主义娱乐博主,对方始终坚持用女性视角去分析娱乐圈的八卦,这给她打开了新的世界。
而随着女性议题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和传播,也让她在赛博世界找到自己的同盟,文西第一次感觉,“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不舒服。”
命名很重要,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也很重要。“男性凝视”、“厌女”、“性客体”、“情绪劳动”这些词在出现之前,女性很难去描述那种让自己不舒服的场景背后是什么。只有当表达变多,且这个过程一遍一遍发生,大家才慢慢明确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不对劲的地方也有了解释。
也有一些关键的时间点,比如2017年。
这一年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MeToo的倡议,鼓励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一运动迅速扩散到全球,引发对性暴力的大规模揭露,女性主义也在这一年成为公共讨论中的焦点。
相关的小说、戏剧也在这一年涌现。台湾作家林奕含写出了以自己性侵经历为原型的小说《房思琪的乐园》,但她自己于2017年4月自缢身亡;讲述两个女性成长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版这一年出版;讲述家庭主妇变成脱口秀演员的影视剧《麦瑟尔夫人》在这一年热播……
李敏深受《房思琪的乐园》的触动,当时正值她在第一份实习工作时被带入酒局,尊严深受伤害。看完这本小说,她第一次感受到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化和凝视,原来一直存在。之后她又去看《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不断反抗的女主角莉拉身上找到了共鸣和力量。
波伏瓦和上野千鹤子是最常被提到的作家和学者。阿允就是这一年开始系统地阅读这些著作。波伏瓦的《第二性》、上野千鹤子的《厌女》给她建构了女性主义的理论地基。
波伏瓦告诉女性,“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上野千鹤子则指出了各种厌女的现象,倡导女性要结成同盟。
两位学者以系统的理论支撑着女性在意识上的觉醒,社交媒体上则有更多女性参与进来,她们不断地发现和表达,从生活日常,从社会事件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男性视角,那些不合理的现象。
这些表达像浪潮一样启发了更多的女性,最终当她们带着发现这些回到自身的处境时,就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眼光。
阿允是广州人,有个小 2 岁的弟弟,她从小就感受到妈妈更喜欢弟弟,仿佛他们三个人才是一家,自己则是外人。她很在意,反抗之下爸妈也会收敛。
这种经历让她对职场中男女被差别对待的情形很敏感。她举例,有一次修电脑,她帮人完成了,对方是正常反应,而男同事完成则会得到更热情的赞美,“我觉得好像广州这边骨子里就比较崇拜男性。”
她也觉察到,跟男女同事打交道之间的差别。女性通常委婉礼貌,但男性更直接,”讲话就是那种,直接丢一个祈使句过来”。
李敏在山东长大,从小就在练习说“不”。因为主体性强,所以一直在反抗,她抗拒敬酒、抗拒父亲的说教,抗拒催逼所有认为理所应当的声音,代价是被惩罚,“我小时候经常被打,甚至扇耳光啥的都是有过的。”
惩罚并没有磨灭她的反抗精神和自我意识,这种天性在进入职场后也未被磨灭,与老板产生过节、对抗说教后拿到低绩效……
不断碰壁的经历有时候让她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女性主义带来的新目光对她来说,更像一种自我确认,确认自己不是真正有问题的那一个。
她也想到,小时候祝福男生都是希望学习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成功,但是祝福女生则是越来越漂亮,“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文西出生于天津,是独生女。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和正反馈很长一段时间保护着她,也铸就了一个钝感的“壳”。但正如文西说的,在新观念的不断地冲洗下,她也有了更新的审视的眼光。
她现在听到对女性领导的污名,比如“情绪化”,会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性别标签。因为当一个男性领导情绪化时,大家往往就事论事,并不会将情绪化与性别关联起来,“我观察下来,男性领导情绪化起来更可怕。”
作为领导,她也能看到,男下属通常会夸大自己的优势,而女性会缩小自己的优点,“比如说一个男生说自己 100 分,那他大概率可能只做到了 80 分;同样情况下,女生恨不得要做到 120 分才敢说自己做到了 100 分。我招过那么多人,大概率的都是这种情况”
她也不会将问女性婚育当做常规项,甚至为此共情对方。有一回面试,一个女生主动跟她说自己上环了,意思是说做了绝育,让她不用担心怀孕的事,她为此心酸,“现在连女性的面试官她们都不敢信任。”
微小的行动
意识的变化,带来目光的变化,更进一步的则是行动上的改变。
阿允、文西是主动走在前面的人。
在前期面试中践行女性主义后,阿允最后进了一家童书出版社,负责品牌文案。
她看到公司过去向用户种草时,默认用的都是“他”,她提出建议,应该改成拼音“ta”。她说服老板,“他”默认的是男孩,但实际用户有男也有女,应该都照顾到,“我觉得我们要给用户传达这样的一个意识。”
办公室有女性同事会不自觉捧着男性,她找到话头,也会在一些闲聊里会引入女性主义的观点。
她并不激进,也不刻意,更在意对方的接受程度。一位姐姐是已婚育女性,她会跟对方聊男孩的教育,不经意间举例儒家文化似乎厌女的例子。
女性的处境都很相似,只要一提点,不自觉就能被感染。阿允后来发现,这位姐姐开始更能看到女同事的优点了。比如一次合作中,她就主动提到,某某女同事好像比男员工更靠谱。
阿允还看到,女同事似乎比男同事更不自信。她于是一有机会就夸她们,起初大家还不适应,因为过去很少有人这么做,但慢慢大家就开始互相鼓励和赞美。
阿允并不将这种行动上升为作为女性的责任感,她只是希望自己这样一点一滴微小的实践能够“动摇一下身边的人。”
文西的女性主义实践里也包括这一点。她已经走到了管理岗,可以做的事情也更多。
晋升或者绩效考评时,她会鼓励女生大胆地争取,“我并不是说额外优待女生,而是在同等的情况下,会去鼓励她们把真实的情况表现出来。”
她鞭策女孩们向男性学习“不要脸”的精神,勇敢去争取,去去打破一些体面和道德感的束缚,“有时候我觉得职场上男生遇到事他们是真的敢去撕,真的敢去当那个不体面的人。但是女生就太好面子,我就说你要更不要做体面人一些。”
分配工作时,她也会刻意去除刻板印象中的分工。比如传统印象中,总认为男性更适合技术类的、数据类的工作,面对这些相关项目时女性会自动退缩。她会主动告诉女下属,“如果你觉得你适合、想做,就告诉我你能做这个事。”
在她的鼓励下,最后女生自己也慢慢发现,自己的能力没有不一样,“一些类似项目,就是这样的女生自己主导并且完成的,不是挺好的吗?甚至比男生更细致。”
意识层面,文西甚至会引导和纠正她们。一次一位工作刚三四年的女员工,被男性同事打压,这位女性主动给对方找补是“太直男了”。但文西像曾经告诉她不应该附和男性用“婊”这个字的姐姐一样,告诉这位女下属,“不要用男性和女性这样的标签来去美化或者贬低谁,他让你不舒服,你就要说他让你不舒服,要勇敢地刚回去。”
苏南(化名)比文西小两岁,是另一家互联网大公司的中层管理。她遭遇过生育后被辞退,和男性高层沟通之后,她也看到了女性走不更高位置背后的复杂原因,比如性别差异下,女性很难与男高层形成忠诚纽带;女性生育的可能性,让她们在作为候选人时就已经不被重点考虑。
她认为自己走到管理层是一种运气,正好赶上了好的时机和好的项目。
不过即便认清了这些,与文西一样,她也仍然有一种职场少数群体的自觉性,会有意识主动为女性拓宽可能性。
比如在与老板的会议或者跨部门会议上,她会更主动参与讨论和发言,她有时甚至刻意表现得更理性也更激进一点,她想让自己成为女员工眼中可以效仿的榜样。
必要的妥协
相比在职场中走得更远的“姐姐们”,刘芳悲观地认为自己作为权力下位者,在职场讲女性主义影响十分有限,因为管理层的女性仍是少数,而这少数中,还有一部分也依然“厌女”。
她认为更重要的是保留着自己女性处境的身份去“上桌”。她觉得自己尚得生存。
尽管是独生女,但她的家庭对她的预设和劝诫也仍然是希望她找一个便于嫁人的好工作,让男性承担更大责任。相比堂兄弟、表兄弟,作为家族的唯一女孩,父母没有给她准备好对等的资源,在老一辈的逻辑里,给女孩的资源是一种馈赠,但是给男孩的是一种义务。
她从小就要在祖辈面前证明自己不比这些兄弟差,为此即便外界标榜的成功并不是她所希望的,但她仍然要努力争取。
而没有父母的倾力支持,她更首要的是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生存下来。这是她在职场中,有时候不得不沉默的心态。
“大家总是谈女性主义如何,但是你落实到生活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割裂。就是你要养活你自己啊。你想独立生活,今天就算痛经,你跟老板请假,但会担心扣工资、影响绩效,是这样的问题。”
李敏也曾因为一个她认为极好的机会,为了在职场“上桌”做过妥协。
那是一个控制欲强的男领导,日常给下属灌输大道理,一不顺他的想法就会发飙,一反抗就被打低绩效。但那个公司、那个团队是她几次跳槽能找到的最好的平台、业务最符合自己职业规划的团队,“就想在那里好好学一学。”
为此,惯于反抗的她最后选择了虚与委蛇。“约他吃了个饭,站在一个仰慕者的角度听他讲各种大道理,后面他就会对你放松警惕,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已经被我洗脑成功。”
但这段经历仍然给李敏带来了精神伤害,她回忆自己那段时间是抑郁的,直到离开了那个工作环境,遇到了新的同事和老板。
戴上社会面具的时候,李敏说的也是,“为了生存,你必须要这样。”
在这个本质上仍是男性主导的职场里,刘芳不希望在规则和权益之外过多谈论“女性主义”,她更希望职场是“去性别化”的。
不过,她描述这种希冀正是一种理想,“我不希望职场里,在正常的法律权益外谈性别。我希望的是今天某一个岗位不用因为男性的稀缺就获得优势。也希望说今天有个很好看的女孩,她被别人说起来不会总是只有好看。”
李敏则会设想,当她成为一个领导、当她手握更多资源时,首要改变的制度是让男女的产假基本相当,“因为这个产假就决定了你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决定了你在这个职场上的你所处的一个位置。女性要投入时间到家庭,公司自然就会把更多的权利给到男性。”
她觉得一个女性友好的职场,也应该对女性在月经期、孕期等特殊时期多一些包容。
李敏也认为,相比让女性成为“强势的、进取的”,她更希望女性不管是天生的或者是后天被教育出来的温和、细腻的优点应该要更多被鼓励被放大。
年轻的女性们都知道在职场里,女性争取平等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刘芳就觉得至少分几步走:第一步是争取权益,用法律来保障女性生存的权益;其次是争取资源和机会,要“上桌”,走到可以决策的位置;最后才是扭转过去根深蒂固的意识,实现全面、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女性们都赞同,女性主义意识的普及,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更理想的社会,“理想情况下,女性主义希望照拂的不只是女性,而是让少数和弱势群体一起拥有平等。”
文章内容无任何虚构,但为保护采访对象,皆采用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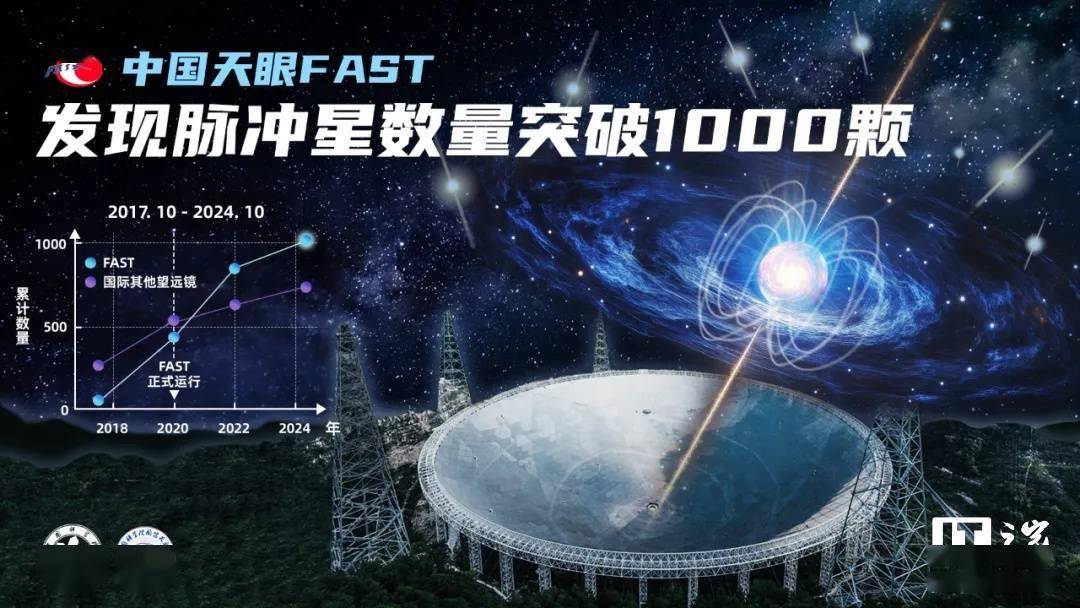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3531号